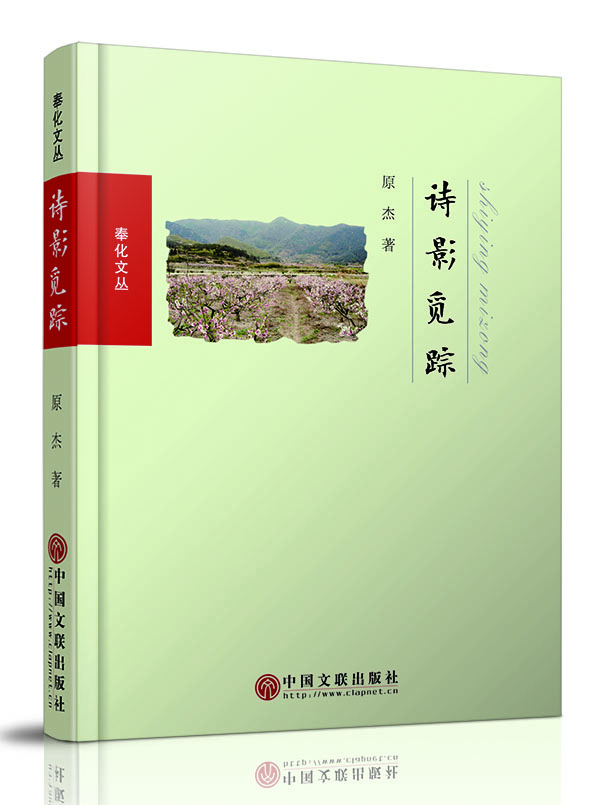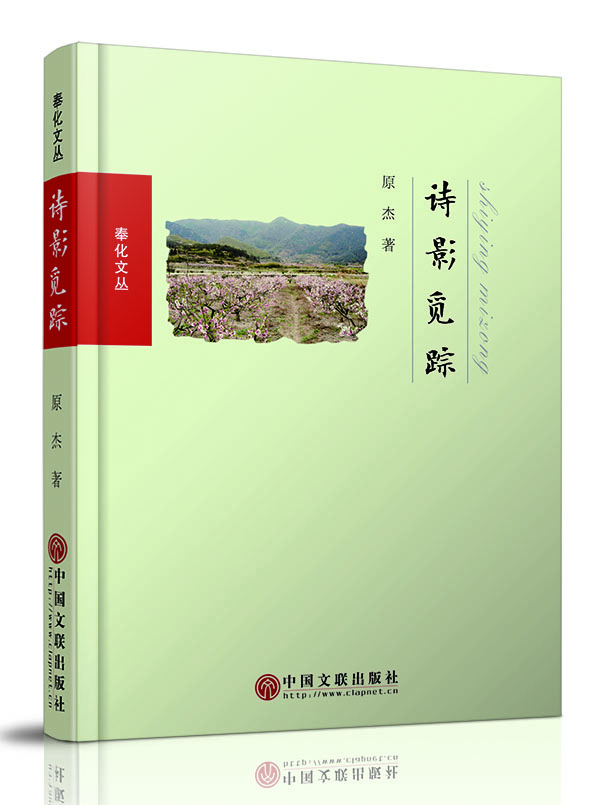 ISBN:978-7-5059-8949-8
条形码:9787505989498
作者:原杰
出版社:中国文联出版社
CIP数据: (2014)第156678号
中图分类号: I267
ISBN:978-7-5059-8949-8
条形码:9787505989498
作者:原杰
出版社:中国文联出版社
CIP数据: (2014)第156678号
中图分类号: I267
开本: 32开
牵手抽象与形象(后记)
偶尔回首,发现几十年间已发诗 500 首、散文 200 余篇。由于诗歌方面先后编辑出版了《蓝花瓷碗》、《东村女子》和《我拉着你的手过田埂》等多本诗集,而散文却还没有结集出版过。因而很想出一本散文集,用来收集这些散兵游勇,让它们有一个“家”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自己一直在思考:如何打通诗歌与散文,或者说让抽象与形象牵手,扬长避短实现共赢,从而探索出一条文学创作的新路来。因为,记得一位名家说过:“散文的最高境界是有自我,有独特的东西,并用独特方法写。”
也许有人会说,把诗归入抽象思维有些不妥,众所周知,诗歌被喻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,是形象思维的顶峰。其实不然,诗、尤其是当代主流诗体朦胧诗,由于采用跳跃式的结构,隐喻、暗喻等手法,还有超出惯常的思维方式(如意识流),让人很难读懂,不少时候需要如同猜谜语一样去破解,因而已演变成形象思维中的一种特殊抽象思维。不是吗?即使像笔者以描写乡村风物为主、已故著名诗人邹荻帆之称为“文风素朴”的现代田园诗,也有好多读者反映“看不大懂”。与此同时,明白如话的散文也需要借鉴诗的情感、诗的韵味、尤其是诗的意境,来提高纯度、增加厚度,创造高度 —— 现在的不少散文太琐碎,特别是缺少诗的激情、韵味与境界。为此,让抽象牵手形象有现实基础,而并不仅仅是一种臆想。可如何让两者牵手?说易做难。众所周知,诗与散文从共生到分家,少说也已有几千载,一直以来都是并行向前。虽在近现代也产生过两者的杂交体 —— 散文诗。可此种文体,仁者见仁智者见智,说好的谓结合了两者的长处,说难听的言集中了两者的缺点:既少了诗的凝练,又没有散文的细腻与明白。换句话说,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结果。而我要的是和而不同 —— 既保留诗凝练隽永的特点,又能提升散文的浓度与烈度。为此,自己设想通过编诗散文集这个平台,以诗“点”文、让诗文融合,并配以自己拍摄的照片方式,营造一种高雅明丽、绵远深情的全新意境。为实现上述构想,具体落实在《诗影觅踪》创作上,表现为“三性”:诗性。首先是诗意的题目“诗影觅踪”,—— 语意为寻找诗人足影与诗的创作痕迹。这样一来,不但提纲挈领确定了诗在文集中的主导地位,同时让诗在文集中的“表演”变得名正言顺:她可以堂而皇之,来去自如。其次是每辑分别用诗歌命名,并相应配一首诗来领衔、营造意境。如第一辑“老家山上的树”,那沧桑、怀
旧的情感如同一场春天里的雨雾笼罩山野那样弥漫全辑文章。其三是绝大部分所选文章都引用了诗,不但使之成为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,而且成为文章的出彩之处;或者,本来便是诗情洋溢的抒情散文,如《家在小城》、《收获季节》、《乡村小路》等等,无疑属于诗性文章。
个性。文集个性集中体现在题目的内涵要求上,即写一位诗人与众不同的成长史:他的足迹,见闻,生活,感情,思想等等。相应的,在构思方面突出一个诗歌创作者的思考高度与观察细度。首先是新,也就是见人之所未见。如第一辑里的《罗隐秀才》、《阿乐嫂》等传奇故事,第二辑里的《从塔竹岭到银坑岭》等游记散文,之前还没发现有人好好写过。即便是同样的题材,落笔的角度也不同。如写美国行的文章可说汗牛充栋,但笔者一不写华盛顿,二不选自由女神,唯独对不起眼的国家艺术馆情有独钟,努力体现诗人的敏锐与独特。其次是“细”,也就是注重细节,通过描写细节,让作品活起来;或者让历史活起来,给人深刻的印象。这在“古镇沙井”、“凉亭文学”、“小城影像:黑白、彩色与数码”等篇章里,演绎得尤为突出。其三是“广”,文集里有传说故事,有游记散文,有诗歌评论 …… 从古到今、天南地北,这既符合诗人天马行空的个
性,同时也营造出诗散文集的鲜明个性。
地域性。人们常说,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。同样道理,越是地域性的便越是诗的。道理很简单:《诗经》为何那么有诗意?无疑,它描写一批最原始的景物,记录一些最简单的劳动,表达一怀最朴素的情感。那是人类童年时代的天真生活,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那么亲切、美好、激动 —— 一种最美的诗情画意!首先是记录本地生活。那生活既是亲切的、又是熟悉的,既是新奇的、又是自然的,既是简单的、又是诗意的。其次是描写本地人物,包括身边熟悉的亲戚朋友,包括接地气的历史人物,其中自然少不了诗人群体,这关系到诗人的传承问题。其三是抒发感受 —— 即使描写外地风景、讴歌大好河山,也以宁波的风景为衡量标杆,由衷表达阿拉宁波人的深切感受:“天安门下听到自己的心跳 / 故都西安让我游历了几千年的时光 / 高楼摩天纸醉金迷 / 我也曾到过香港 / 只是气喘吁吁跟不上那里的速度 / 又回到我江南村庄”(见拙作《春天时我还想去一个地方》)。
总而言之,如果说题目《诗影觅踪》是原点,那么从短题出发到长引,到 5 个专辑,再到具体的 75 篇文章,诗意呈明显的散发状。其中,抽象与形象牵手紧松有序,共同演绎精彩,着力创造一种清新的、令人刮目相看的效果。当然,尽管用心良苦,但牵手是否成功,会不会属于“拉郎配”?换句话说,有没有达到散文的最高境界,写出特色与自我?其客观效果检测便只能借助诸位读者朋友的一双慧眼了。